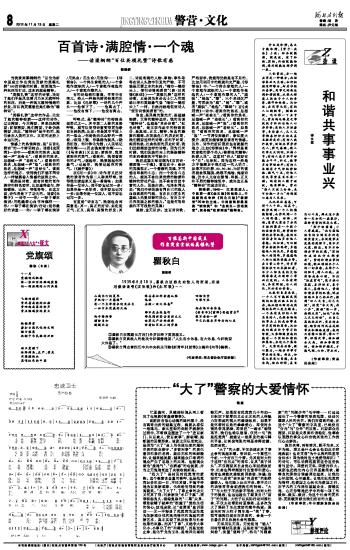储瑞耕
当我读到梁桐纲的“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礼赞”100首诗稿的时候,深深地为一种东西所打动,这东西就是精神。
“英模礼赞”这样的诗歌,决定了她们不是风花雪月乃至无病呻吟的东西,而是一种高亢精神情绪的抒发。所以我更愿意把她们称为“精神诗”。
“英模礼赞”这样的作品,注定了她的精神特质——这样的诗作,过去需要,今天需要,将来仍然需要;前辈需要,我们需要,子孙仍然需要,因此,“精神诗”是不朽的,她们会在人类的文化、文明的史册上永远闪光。
情感上的热情奔放,是“百首礼赞诗”的一个鲜明特点。请看《戎冠秀》一诗中——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老会长”,/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老校长”,/ 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娘”,/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老站长”。读到这样的地方,使得我们不能不同诗人一样被裹卷入情感的波涛之中。
既然是诗歌,就有诗歌的创作规律和特色要求,比如遣辞造句,押韵顿挫,比兴,夸张等等,在这方面,诗作者是下了功夫的。请看《向警予》一诗中——你/ 一辈子都在演讲/用笔蘸着心血书写稿样……你/ 一辈子都在演讲/行动/是你最好的讲堂……你/ 一辈子都在演讲/用热血/ 用生命/用信仰……《邹韬奋》:一个终生拿笔的人/一个拿笔作旗帜的人/一个拿笔作枪炮的人/一个拿笔作犁的人
有的诗结构和意境,寻常中有突兀,给人一种相当鲜明特别的印象,比如《毛泽覃》一诗的几个开头——他倒下了,……他离去了,……他没有倒下,……他没有离去,……
呼唤式,是“精神诗”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。其中第二人称的直接呼唤,就可以使得诗意变得更为亲切自然热烈。比如:你是冀中平原上的一架山,/你是鲁西北山野的一棵松,/跃马上鞍,你驰骋为旋风,/骁勇征战,你冲锋化为箭,/人民铭记着你啊——/历史镌刻着你啊——。(《马本斋》)又比如:读到你,我便读到你的英气,/看到你,我便看到你的才气,/想起你,我便想起你的豪气,/记起你,我便记起你的骨气。(《杨开慧》)
在《闻一多》中,诗作者又把诗歌的读者作为第二人称来呼唤,使得我们读起来又是一番滋味:如果你是一位诗人,请不要忘记闻一多/如果你是一名学者,请不要忘记闻一多/如果你是一位国人,请不要忘记闻一多。
有道是“诗言志”,我想包含两层意思:其一,真正的好诗,必定是正气、正义、真理、真情的抒发;其二,诗是客观的人物、事物、事件等等在诗人头脑中引发的产物,不可能是无源之水的东西。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宵”(唐·刘禹锡《秋词》)——“英模礼赞”这样的诗歌,正是因为革命志士仁人的英雄壮举和英雄豪气像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一样,自然而然地促使诗人“便引诗情到碧宵”的。
信念,是灵魂的聚光灯,是超越物质、世俗的精神追求。我的所谓“精神诗”,也就是“革命诗歌”、“红色诗歌”,是文学作品中的特殊部分,是真理、正义、精神、信念的凝聚和精粹。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,我们需要这样的诗歌;在和平时期,经济转轨、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,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诗歌。因为任何时候,我们民族的向上的提振精神的东西都须臾不可缺少!
我把这篇文章定题为《百首诗·满腔情·一个魂》,意思在于:组诗的灵魂很正。一个萎靡的灵魂,不可能有昂扬的斗志;而一个没有斗志的人,就决不会出来优秀的物质和精神的劳动产品,决不会有价值丰富的人生。民族亦然。毛泽东同志说: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,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,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”这是何等昂扬和不可战胜的灵魂!
诚然,金无足赤。这百首诗歌,严格要求,我觉得仍然是有不足的,比如用词用字的粗疏和欠严整,《邹韬奋》中:“一个终生拿笔的人/一个拿笔作旗帜的人/一个拿笔作枪炮的人/一个拿笔作犁的人”,“旗帜”、“枪炮”、“犁”,三个名词欠严整,可否改为“旗”、“枪”、“犁”,或者“旗帜”、“枪炮”、“犁铧”?在《戎冠秀》一诗中: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老会长”,/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老校长”,/ 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娘”,/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“老站长”。如果把“看到你的姓名,总想喊一声‘娘’”一节调位到最后,亲切度大提升,就更加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。另外,诗作的前后照应也有疏漏的地方,比如《邹韬奋》中:“同样是喜欢拿笔的那个伟人/称赞他的精神/热爱人民”。这里对“伟人”就要有个“注”:毛泽东。因为这样一些地方不能满足于我们这一代人明白,如果不加注释,00、90、80、70后的读者就会很隔膜。然瑕不掩瑜,掩卷诗稿,仍令人亢奋在激情、昂扬、正义和不屈的精神愉悦中,或许这正是“精神诗”的成功所在。
储瑞耕,1946— 江苏武进人。中国第一家《杂文报》的创始人,中国新闻名专栏《河北日报》“杨柳青”20年的主笔,中国新闻界最高奖“韬奋奖”和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、国务院“政府津贴”获得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