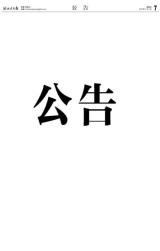| ||
|
□ 姚秦川
准确地说,在乡下,从腊月二十三日的“小年”那天起,就正式拉开了过大年的帷幕。
此时,不管你身居乡下的哪个地方,是在新盖的两层楼房里,还是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,远远就可听见从什么地方传来的锣鼓声,欢快,闹腾,热烈,震天响。间或,夹杂有高昂婉转的唢呐声,清脆的鞭炮声,孩子们的欢叫声。乡村的年,就在这种奔腾喧闹声中,进入了自己的角色。
我的家在渭河边上。我们那里的年,和许多个乡村的年一样,也是从腊月中下旬就开始了。不知何时,村里的大锣鼓早已被人抬出来了,喜欢扭秧歌的婆姨们也早早换上了五颜六色的服装,有红的、绿的、粉的,似若花朵,艳赛桃花。
很快,锣鼓敲起来了,秧歌扭起来了。人人脸上挂着笑容,说着开心的话,聊着闲散的事。孩子们此时最快乐了,大的小的都放了寒假,跑着叫着打闹着,不像平日里,难得一见孩子们的笑声。
在我们村,有专门负责锣鼓秧歌队的队长。千万别小看了这个队长,在过年那段时间里,所有的拜年和表演事宜,全由队长一人负责。而每个人的腰包,都要仰仗队长那张能说会道的嘴。
转眼,就到年根下。家家户户在大门上贴对联是必不可少的事情。父亲在世时,我会和父亲一起贴上火红的对联。有时,为了对联里内容的深浅,父亲还会和我争讨几声。待对联贴好后,下一步就是在大门的屋檐下挂上火红的灯笼,灯笼越大越好。
当然,灯笼并不是每家都挂的。在我们那里,一般情况下,只有娶了媳妇的人家才挂。灯笼是娘家人送来的,寓意不言自明,挂灯笼照舅。
此时,最忙碌的却要数家里的那些女人了。她们统一在厨房里忙碌着,并且全村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:蒸馍。在我们村的习俗里,腊月二十九三十那两天,每家每户都要蒸馍,少则二三锅,多则五六锅。
很快,天就麻麻黑了。这时,村里之前演练很久的锣鼓声就会适时地响起,他们开始了每家每户的拜年活动。每到一家,主人为讨个吉利,或两包烟,或几十块钱零钱。没有人在乎这些,大过年的,谁不想讨个吉利,添个彩头呢?
一帮小屁孩跟在锣鼓队的后面疯跑,遇到有主人送给的糖瓜子之类的东西,带队的队长总会慷慨地全部散给孩子们,引来一片欢呼声。
在我们家,大年三十给长辈拜年,是必不可少的事情。先是去了二叔家,给二叔拜年。然后回来,再给父母拜年。象征性的,父母会将压岁钱塞进女儿的口袋里,女儿也总会乖巧地祝爷爷奶奶长命百岁。
之后,全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,看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。说说笑笑,气氛热烈。在我们那里,包的饺子一般都会等到大年初一才吃,图的就是开门团圆。
此时,小小的山村早已被震天响的鞭炮声掩盖住了,家家户户灯火通明。孩子们第二天要穿的新衣服,父母早已准备好,放在炕头上了;同样第二天要招待村里客人的烟酒,也早已拿出来,摆在桌上。屋里屋外,被红的灯笼红的鞭炮红的对联包裹着,瞧着喜庆,看着欢心。
乡村里的年,就在这浓浓的夜色中,正式拉开帷幕,变得更加热烈,更加让人难以忘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