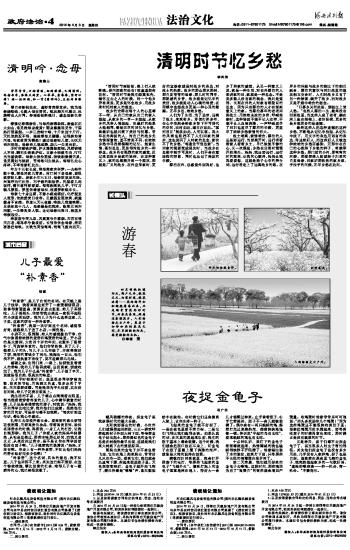李凤伟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清明时节是我们祭奠祖先,缅怀过去之人的时候,对一个他乡异客来说,更多是怀念故乡,用故乡来衬托对家人的想念。
故乡的诠释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一样,从自己的家从自己的亲人想起,从家乡的一草一木想起,从家乡的风俗人情想起,但最后的结果大抵相同,都是无尽的回忆与乡愁,到最后也就只剩下美好与祝愿。常年在外奔波的人,对自己的故乡尤为情深意浓,道不清说不明,在浓浓乡愁中寻找着模糊的记忆,触景生情,落泪思思,更显得对故乡的一种眷念。故乡具有强烈的家的感觉,反过来说故乡是家的延伸,在某种意义上,家的思维提升到一个层次,那就是广义的故乡,在外宣传家时,更好的宣扬家就是对故乡的表达,对故土的热爱。故乡的那山那水那树,那白发苍苍的母亲,那儿时的同伴,那熟悉的乡音,故乡就是记忆中的美好,故乡就是动人心魄的母爱,在困顿中念想故乡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无尽乡思,浓浓乡愁。
人们为了生活,为了追求,远离了故土,来到客乡。即便打拼多年,在心中依然会给家乡留下不可替代的空间,农村如此,城市亦如此。“狐死首丘”兽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再大的风雪也阻挡不了人们回家的脚步,这也说明了人对家的思念,割舍不了的乡愁,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当回家的渴望变成现实时,当故乡在思维中触手可及时,人们不会在意旅程的劳累,同时也忘记了奔波的辛酸。
漂泊在外,总感觉外面再好,也少了些家的感觉,从另一种意义上说,家是一种生活,对在外漂泊的人来讲家的话,家就是一种思念。不是说多数人没有家的概念,我只是觉得,长期在外的人对家有着殷切的思念,因为只有漂泊的人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。当漂泊暮年的老者回到故土,用浓浓未改的乡音,呼喊母亲时,这种场面不能不让人动容,不能不让人血液沸腾,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的辛酸,更道尽了浓浓乡愁亲情的伟大。
故土难离,亲情难舍,漂泊的人还是要远行,当要离开时,远行者看着亲人看着乡土,早已恢复平静的心,又一次提起,乡愁在分别时慢慢开始增生。妈妈,我还要远行,远行时的离别,让我的心颤抖,妈妈让我再看看您,这就是游子心中的潜台词,远行者走上了远离故乡的路。在异乡的体验与故乡的相比下的相互融合,漂泊的意识与回归故里的想法相互交合时,人们对故乡又有了另一种解读,绕开了故乡,而对故乡又是矛盾中难舍的想念。
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 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有些人漂泊一生,最终没有回到故里,当这些人成了老者,躺在床上坐在摇椅上,老泪纵横,更多的是乡愁更多的是遗憾。
最终这些人把这种遗憾把这种乡愁,不断地从记忆中拾起,从记忆中放下,用文字的表达用语言的表达,传述给后人,而这些后人又被这种浓浓的乡愁所感染,无形中在自己的心底埋下乡愁的种子,将继承这种乡愁。那门前的小河,那弯弯的河柳,那看着路人盼望游子归来的白发母亲,回家后那热热的家乡菜,手拉手的问候,无尽乡愁在此间。